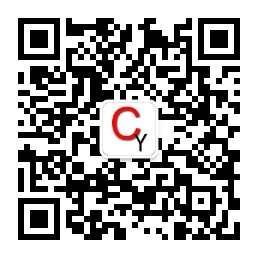内蒙古-鄂尔多斯鬼城
近几年来,“鬼城”成为媒体批评房地产泡沫时常常引用的一个现象。所谓“鬼城”,一般来说,就是在该区域内兴建了大量住宅项目,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:大量住宅空置,并没有如期引来人流。
去年,国家发改委曾对12省区做过“新城区”调查,发现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.5个新城、新区,而且许多新区动辄就是数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大手笔规划。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动力来造新城?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,而城市原有城区无法容纳下这么多的人口,因此必须在城市周边另辟新城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.36亿人,而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周围,因此建设新城也就在所难免。以上海松江区为例,截至2013年底,松江常住人口已经过200万,而户籍人口大约共有60万不到。在这个背景下,建设新城区也就水到渠成。
为什么很多新城会成为鬼城?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超前。如果再回到10年前,那么现在看起来很多很繁华的新城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“鬼城”。以上海浦东为例,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3187445人,但是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已经达到5044430人,十年共增加1856985人,增长58.26%。10年前上海浦东很多地方还是空空荡荡,而现在这些地方已经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。
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这些新城未来都会成为闹市区?这倒不一定。从这几年中国的人口流动趋势来看,中西部向东部流动、农村向大城市流动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: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省份都是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,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县城的常住人口都少于户籍人口。而且从可见的将来,这个人口转移趋势还不会发生改变,如果将新城建设在不是人口增加的区域,那么新城还是会变成鬼城。
以浙江省为例,在全省58个县(市)中,2010年常住人口数高于2000年的县(市)为31个;而在常住人口数最少的20个县市中,只有武义、三门、云和和岱山四个县的常住人口数在增加,其他县(市)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,很多县的常住人口数更以20%的速度在减少。如果再计算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,那就更有意思。全省58个县(市)中,只有17个县(市)的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,不少县城的常住人口甚至只有户籍人口的70%。
尽管浙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,而且其县域经济也被视为国内的领头羊,但是即便如此,还是抵挡不了这些县人口变少的趋势。不过有意思的是,即便这些地区的人口在减少,但这些县城建设新城的决心却不变。
还是以浙江某中部县城为例。根据2012年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××县域总体规划的批复》来看,该县中心城区规划面积228.06平方公里,2020年人口规模按县域常住人口23万人、城镇常住人口15万人、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0万人规划。但过去十年,该县的常住人口都是在减少,如果一直持续过去十年间的人口变动趋势,2020年的常住人口无论如何也达不到23万,甚至可能只有16万。这意味着以23万人口为目标而投入的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会被浪费,当然,这个县城所建造的新城也可能是“鬼城”。
难道地方政府没有看到人口流动的趋势?显然不是,各地地方政府都有统计部门,明显知道人口的流向。为什么明明知道人口在减少,但是各级地方政府还是愿意大兴土木建设新城?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过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,使得它们认为建设新城的成本完全可以获得弥补,而且通过建设新城还可以增加gdp,何乐而不为呢?
归根结底一句话,那就是卖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低估了“鬼城”的潜在风险。在过去十多年中,那些最早以土地为抵押品进行新城开发的城市几乎都取得了成功: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,深圳、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迫尝试仿效香港,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,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,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———这就是“土地财政”的由来。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,“土地财政”不断完善。急剧膨胀的“土地财政”,帮助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: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,甚至还建设了超前的基础设施———如新城。
但是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事物,房地产也不例外。尽管在过去十年城市房地产如火如荼,但是一旦城市土地供应超过实际需求,那么价格就会发生回落,目前大规模建设的新城也是如此。可以预见,很多县城所建设的新城区可能都逃脱不了“鬼城”的命运;如果仅仅是“鬼城”倒也罢了,更要命的是所有的这些新城建设都是通过银行信贷,最终这笔债务会由当地居民承担,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。
这才是“鬼城”的真正风险。